书论 | 两汉——赵壹《非草书》
2017-12-09
赵壹(公元122—196年),字元叔,古汉阳西县(今甘肃陇南礼县)人,东汉辞赋家。是东汉时期与书法家敦煌人张芝,赵壹石像 思想家镇原人王符齐名的陇上三大家之一。他体格魁梧,美须豪眉,相貌超群,性格耿介狂傲,举止独特,铮铮铁骨,顶天立地。本篇《非草书》以长篇专论强烈非议当时刚新兴的草书艺术,一则否定草书的功用,再则抨击时人痴狂学草书的风气,欲学者返于仓颉、史籀的正规文字,用心思于儒家经典之上。最后虽终势不可回,草书仍然持续由隶草、章草以至今草、狂草一路发展。然从中亦反应出东汉草书艺术蓬勃发展的事实,足以弥补正史上记载的阙漏。
赵壹的《非草书》在书法理论史上有十分重要的地位,具有里程碑的意义。这篇文章的基本观点,是反对当时张芝、罗晖、赵袭等人对草书如痴如醉的追求。赵壹认为这些草书家没有去研究圣人之道和治国之道,而来研究一个 “上非天象所垂、下非河洛所吐、中非圣人所造”的 “小技”——草书,这一举动有悖圣人的教训。无论从哪个角度看,赵壹的 《非草书》都可以被看成是一篇反书法的文章,可是历代众多的书法论文选本都把这篇反书法的文章摆在第一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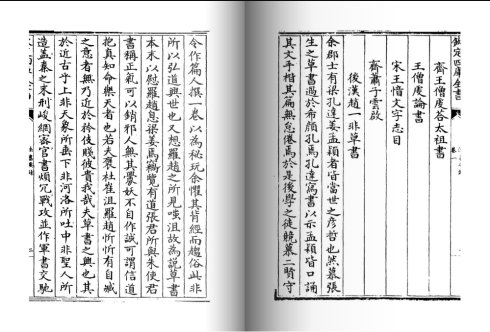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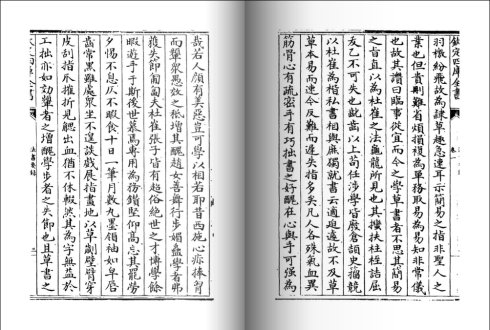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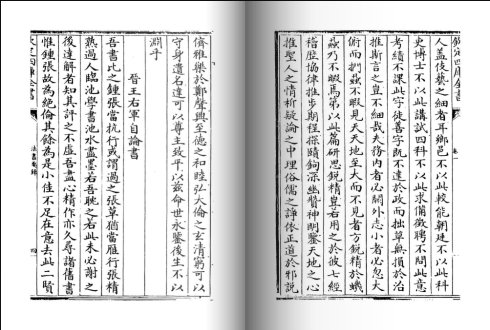
《非草书》原文:
余郡士有梁孔达、姜孟颖,皆当世之彦哲也,然慕张生之草书过于希孔、颜焉。孔达写书以示孟颖,皆口诵其文,手楷其篇,无怠倦焉。于是后学之徒竞慕二贤,守令作篇,人撰一卷,以为秘玩。余惧其背经而趋俗,此非所以弘道兴世也,又想罗、赵之所见嗤沮,故为说草书本末,以慰罗、赵,息梁、姜焉。
窃览有道张君所与朱使君书,称正气可以消邪,人无其衅,妖不自作,诚可谓信道抱真,知命乐天者也。若夫褒杜、崔,沮罗、赵,欣欣有自臧之意者,无乃近于矜忮,贱彼贵我哉!
夫草书之兴也,其于近古乎?上非天象所垂,下非河洛所吐,中非圣人所造。盖秦之末,刑峻网密,官书烦冗,战攻并作,军书交驰,羽檄纷飞,故为隶草,趋急速耳,示简易之指,非圣人之业也。但贵删难省烦,损复为单,务取易为易知,非常仪也,故其赞曰:「临事从宜」。而今之学草书者,不思其简易之旨,直以为杜、崔之法,龟龙所见也,其蛮扶拄挃,诘屈犮乙,不可失也。龀齿以上,苟任涉学,皆废苍颉、史籀,竞以杜、崔为楷;私书相兴:「庶独就书,云适迫遽,故不及草。」草本易而速,今反难而迟,失指多矣。
凡人各殊气血,异筋骨:心有疏密,手有巧拙;书之好丑,在心兴手,可强为哉?若人颜有美恶,岂可学以相若耶?昔西施心疹,捧胸而颦,众愚效之,只增其丑;赵女善舞,行步媚蛊,学者弗获,失节匍匐。夫杜、崔、张子,皆有超俗绝世之才,博学余暇,游手于斯。后世慕焉,专用为务;钻坚仰高,忘其疲劳;夕惕不息,仄不暇臂穿刮,指爪摧折,见(角思)出血,犹不休辍。然其为字,无益于工拙,亦如效颦者之增丑,学步者之失节也。
且草书之人,盖伎艺之细者耳;乡邑不以此较能;朝廷不以此科吏;博士不以此讲试;四科不以此求备;正聘不问此意;考绩不课此字。善既不达于政,而拙无损于治,推斯言之,岂不细哉?
夫务内者必阙外;志小者必忽大。仰而贯针,不暇见天;俯而扪虱,不暇见地。天地至大而不见者,方锐精于针虱,乃不暇焉。第以此篇研思锐精,岂若用之于彼七;稽历协律,推步期程;探赜钓深,幽赞神明。览天地之心,推圣人之情;折疑论之中,理俗儒之诤;依正道于邪说,侪「雅」乐于郑声;兴至德之和睦,宏大伦之玄清。穷可以守身遗名,达可以尊主致平,以兹命世,永鉴后生,不以渊乎?
《非草书》译文:
我所在的汉阳郡(今甘肃境内)有士人梁孔达和姜孟颖二人,都属当代贤哲。然而他二人对张芝草书的仰慕甚至已超过对孔子和颜渊的仰慕。梁孔达摹写张芝的草书给姜孟颖看,都是边念诵着张芝的文章,边一板一眼地临写,不敢有一丝怠慢。因此晚辈後学们也都很敬重他,等他写完全篇後,每人都拿走一卷,视为不轻易示人的珍藏。我担心他们弘扬草书是有悖正统且趋於流俗,此也并非弘扬大道及有益於世风,加之又想起张芝曾讥笑蔑视过罗晖与赵袭,所以我想来谈谈草书的原委始末,权作对罗晖和赵袭的慰籍,并期望梁孔达和姜孟颖也能罢手。
我看张芝(又名张有道)给太仆朱宽所写的信,说正气可以消除邪恶,人们若无罪过,邪恶也不会自行跑来,此也就真可以说是信守大道-保持真性,安守命运-乐於天道了。至於张芝褒扬他所师法的前辈杜度与崔瑗,蔑视後来的罗晖和赵袭,且颇有自鸣得意之状,莫非对自己的书艺过於自负,轻人重己麽!当初草书的兴起,难道很古麽?(我觉得草书)上不是(庖羲氏)仰观天象所得,下不是河洛二水所吐的河图洛书,中不是人间圣贤所造。是因秦代末年时,刑罚严酷法律严密,官家的公文繁琐冗长,你来我往的战事又多,军事公文往奔传送,紧急文件满天纷飞,所以出现了潦草的隶书,为赶时间提速度而已,只求简便快速地传达指令,但此并非圣人所推崇的主旨。
但(草书)贵在删繁就简,变复杂为简单,目的就是为简便而简便,并不是正常规范的写字方式,所以当时人们都赞成的理由是:能临时就急行事。而如今学习草书的人,不考虑当初是求就急简便的目的,武断以为就是杜度和崔瑗的笔法,甚至视如龟龙般神圣。且以为其笔划的大起大落,曲折多变,是草书不能缺少的。而八岁以上的孩子,只要开始上学,写的都不是仓颉-史籀所创造的字,反以杜度和崔瑗的字为样板。民间个人往来书信时,每每也说:因时间关系,所以字写得草了些云云。草书原本是简易快速,如今反觉得难写或写得很慢了,这也就失去太多草书的本意了。
大凡人,气质秉性不同,体力精力各异,心有粗细之分,手有笨巧之别,而字的好坏,如何能强求呢?亦如长相有美丑,岂是一学就能与人家一样呢?过去美人西施患了心痛的病,手捂胸口而紧蹙眉毛,而一群愚昧者也去学她,反而越学越丑。赵国女子擅长舞蹈,举手投足妩媚娇艳,效仿的人不但什麽也没学会,反因不知如何而爬着走了。杜度-崔瑗-张芝,都是有超凡脱俗-绝世才华的人,在博闻强记的闲暇之时,写字只是随手的事儿。可後人学习并仰慕他,却只致力於写字,以为就是钻研艰深,仰慕高难,甚而忘记辛苦疲劳,日夜不停地练,连饭都顾不上吃;十来天就写坏一枝笔,个把月便用尽数丸墨;衣领与袖口全都被墨蹭黑,嘴和牙也是黑的;即使大家坐在一起,聊天也不踏实,也要以手指做笔在地上写着,或拿着草秸在墙上划着;臂肘磨穿了,皮也硌破了,指甲也折断了,两腮也凹陷了,依旧坚持不懈;但所写出的字,并没多大长进,亦如仿效西施的人一样反而越学越难看,也像模仿赵国女子舞蹈的人反而不会走路了。
而且这些写草书的人,不过是些掌握雕虫小技的人而已。加之乡里并不以写字技艺作为本领来衡量,朝廷也不以此来科举取士,博士更不以此作为讲评考核,四门科目中也没有写字一科,招贤纳士也不会关注你字写的好坏,业绩考核也与写字无关,即使字好也与政无补,字坏也不妨碍治国,由此说来,写字其实是件微不足道的事。专注自我的人,必缺大眼界;志向太小的人,必无大作为;如同低头捉蝨子,哪有机会看天;而你看不见浩天广地,只专注在小虫子上,也就什麽也看不见了。
即使(梁孔达摹写张芝的)这篇草书再钻研精心,(我看)还不如用在对儒家经典的钻研上,诸如对天文历法的考察研究,推算一下天象运行的时间周期,探寻思索其中奥秘,潜心解读宇宙神明,观察天地的心境,推究圣人的情怀。解开疑惑的问题,理清俗儒的争执,用正道来驳斥邪说,让雅乐来拨乱郑声,倡导和谐至上的德行,弘扬顺应天道的大法。退可以恪守节操-留下英名,进能够尊崇君主-辅国治平,以此安身立命,也可成为後人学习的典范,其意义不是更大更深远吗!